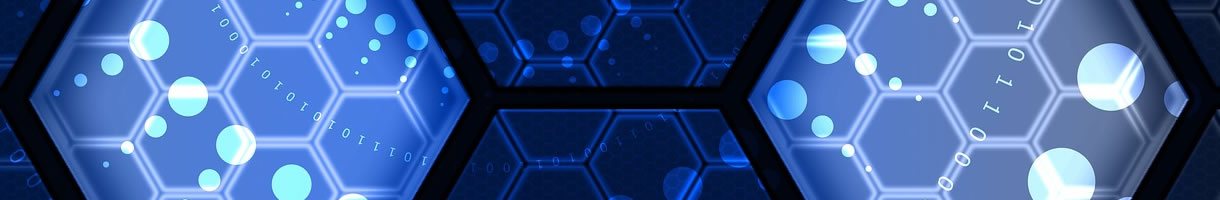金融霸权与工业根基:英美历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金融霸权与工业根基并非天然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需要有意识、前瞻性的国家战略来加以平衡的动态关系。本文通过对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历史霸权的深度剖析,揭示了这一核心悖论。英国的“相对衰落”源于其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忽视和金融资本的海外逐利,其金融霸权只是加速了工业基础的侵蚀。相比之下,美国的“去工业化”则更多是主动的产业升级与价值链重塑,其强大的金融体系成为资本流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引擎。然而,对金融霸权的滥用正在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反过来促使美国不得不重振实体工业。对中国而言,历史的启示是深刻的。中国必须坚持以工业为立国之本,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工业升级和全球化的战略工具,而非最终目标。战略上,应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资本流向的宏观调控和全球治理创新,探索一条金融与工业协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规避前任霸权所犯的错误,从而在未来的全球格局中巩固其综合国力。

全球霸权周期中的核心悖论
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登顶,往往伴随着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乃至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种金融霸权带来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核心战略悖论:当金融资本因其超然的地位而获得超额利润时,如何防止其对本国实体工业基础形成挤压,最终导致工业霸权的丧失?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复杂问题,通过对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这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为正处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提供历史镜鉴与战略建议。报告将主要运用两个核心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展开论证:
首先是“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它揭示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所面临的内在矛盾。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持续对外输出货币以满足全球的流动性需求。然而,这种持续的货币扩张会导致该国出现长期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增加,最终威胁到其货币的币值稳定和国际信任。从深层次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浪潮,都是这一内在矛盾的体现。
其次是“荷兰病”(Dutch Disease),该理论最初用于描述荷兰因天然气出口繁荣而对本国其他工业部门造成的负面影响。当一种特定资源(在本文中指代金融霸权带来的“铸币税”)的异常繁荣导致本国货币升值时,就会削弱其他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单一化和工业基础萎缩。这一理论为理解金融霸权如何通过汇率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提供了分析工具。
通过将这两个理论框架应用于英美两国的历史实践,本文将超越简单的因果论,揭示金融霸权与工业基础之间更复杂的动态关系,并为中国提供有理有据、切实可行的战略指引。
日不落帝国的黄昏:金融的盛宴与工业的隐疾
19世纪的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革命成果,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霸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凭借煤炭、钢铁和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工业品的首要生产者,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到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28%的工业品,其中煤炭占60%,钢铁占50%,棉纺织品占50%。早期,英国的工业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其前瞻性的产业扶持政策,例如禁止进口印度棉布以保护本国纺织业,并通过向技术发明者授予爵位和奖励来推动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英国的金融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伦敦金融城在17世纪政治变迁后崛起,其核心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促进了公共债务体系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金融城通过其庞大的金融网络,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全球贸易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支持。在这一黄金时期,工业和金融形成了良性互动,互为支撑。

然而,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开始面临挑战。工业革命进入以重工业和电气为动力的新时期,而英国的反应相对迟钝。德国和美国等后发国家凭借新的技术和更具活力的企业,在钢铁、电气等领域迅速崛起,对英国构成了强劲竞争。
与德国、美国等国相比,英国的教育体系也存在明显短板。19世纪的英国,民众教育被忽视,工厂里会写字的人寥寥无几。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于,英国的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且大学正规教育与企业科研严重脱节。这种技术和教育上的滞后,导致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回报率相对下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强大的金融霸权和庞大的殖民体系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新的出路。从1870年开始,英国的海外投资额开始超过国内资本生成,金融资本转向全球寻找更高的利润。英国逐渐从“世界工厂”蜕变为一个“寄生性”经济体,依靠国际垄断盈余来生存。因此,英国工业的衰落并非金融化的唯一结果,而是在其工业体系固化、创新乏力之后,金融资本逐利天性加速了这一进程。金融霸权,在此阶段,反而成为了釜底抽薪的工具。
面对工业的相对衰落,19世纪末的英国政府最初坚持自由放任政策,拒绝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有限的应对在强大的国际竞争面前收效甚微。进入21世纪,面对持续的工业挑战,英国再次将振兴工业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例如“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和“工业竞争力计划”。这些战略旨在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投资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支持电动汽车研发和生产等措施,来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然而,这些当代政策仍面临诸多挑战。英国的市场活力在近几十年来持续放缓,且地缘政治因素(例如脱欧)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英国工业部门的活动下降尤其明显,表明其复兴之路依然充满阻力。
美元的悖论与觉醒: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钟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凭借美国的强大国力,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为了维系其作为全球主要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必须持续不断地向世界提供充足的美元。根据“特里芬难题”,美国通过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对外输出美元。这种机制使得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后,主要流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领域。这导致美国经济本质上成为一个“债务经济”,用债务维持着繁荣的假象,而金融资本过度膨胀,产生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
尽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5年的13%降至2024年的10%),但这并非简单的工业衰落,而是一种战略性的产业结构转型。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便与英国一道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其直接原因是企业盈利下滑、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居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服务型需求增加,以及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美国主动将低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外包,同时将资本和人才集中到价值链的顶端,如研发、设计和品牌管理。这种“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范式,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尽管直接从事生产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但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岗位数量庞大,且附加值极高。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将非直接岗位计算在内,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约为1500万,远高于通常统计的数字,而宽口径下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接近17%。因此,美国霸权的韧性在于其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重塑,成功地将“荷兰病”的效应从“产业萎缩”转变为“产业升级”,将金融霸权带来的资本红利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动力。

美国政府对制造业衰落并非毫无作为。早在1791年,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提出通过补贴、关税等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里根经济学”,通过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管制来刺激商业投资,尽管其军事开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预算赤字。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集中于制造业,但通过一系列政策,美国经济在1983年后戏剧性地复苏。进入21世纪,面对供应链风险和地缘政治挑战,美国政府已将制造业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形成了两党共识。通过高额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方式,美国政府正积极吸引制造业回流,尤其是在初级金属产品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这些驱动因素包括高关税、政府补贴、地缘政治影响以及自动化技术的采用。
龙的抉择:人民币的征途与工业的长城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左右。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这使得中国在推进货币国际化时,拥有英、美等霸权国在崛起初期所不具备的、坚实的工业基础优势。然而,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升级挑战。尽管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比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下降苗头。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四基”薄弱,即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的薄弱,这是制约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症结所在。此外,国际竞争加剧和外部技术封锁也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坚实的工业基础支撑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深化。根据2024年的报告,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已连续十个月保持全球第四位,并在全球贸易融资中位列第二。人民币在货物贸易跨境收付中的比例持续提升,双边货币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更将为中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有力支持。然而,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也将面临潜在风险。其中之一便是“不可能三角”的客观存在,即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实现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当人民币被广泛用于国际结算和投资时,可能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带来新的挑战。

鉴于英美两国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当前的国情,以下三条战略建议对于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巩固工业霸权至关重要:
战略性产业政策
中国不能重蹈英国因缺乏前瞻性产业政策而衰落的覆辙,也不能简单模仿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进行的高端产业外包。中国应立足于自身完备的工业体系,通过“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规划,聚焦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四基”薄弱环节。这需要政府持续投资于基础研发、人才培养和产业技术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并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资本流向的宏观调控
为了避免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所带来的“纸面财富”繁荣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风险,中国必须通过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而非仅仅是房地产和虚拟经济。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铸币税”红利,应被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创新的动力,而非成为加剧金融资产泡沫的催化剂。
制度与治理创新
吸取美元霸权滥用所引发信任危机的教训,中国应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治理创新相结合。这不仅包括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应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非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从而为“去美元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将服务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经济秩序,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支持。
我们唯一的未来:金融与工业的协同发展之路
金融霸权并非必然导致工业衰落,但其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和“荷兰病”效应需要有意识的战略管理来应对。英国的经验是警示,即缺乏前瞻性产业政策和对教育技术的持续投入,金融霸权反而会成为工业衰落的催化剂。美国的经验则展示了一种更具韧性的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重塑,将金融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尽管其对金融霸权的滥用正在引发深远的“反噬”效应。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拥有英、美等霸权国在崛起初期所不具备的、完备工业体系的独特优势。中国应将此视为战略核心,将金融发展作为工业升级和全球化的工具。这要求中国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既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铸币税”红利,又要通过精准的产业政策和资本流向调控,将这些红利有效地转化为解决工业技术瓶颈和结构性挑战的动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深刻理解历史的教训,并结合自身国情,走出一条兼顾金融与工业协同发展的中国模式。